西安市东门内北侧,坐落着一座东岳庙。按常理说,东岳指的是山东泰安的泰山,在泰山脚下建东岳庙是自然的。看看五岳之地,哪一处没有岳庙。陕西本来就有西岳华山,华山脚下有西岳庙。那么,西安城内的东岳庙,是因何而建的呢?
西安东岳庙
山东泰安的东岳庙,也叫岱庙。泰山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山”,“天下独尊”,它号称是五岳之首,是山的岱宗。东岳庙也多了一个名字。泰山面向东方是开阔无垠的大地,向东延伸到了大海,高耸的山势,登顶可达天际,如置身于天穹仙境。历史上各个时期,皇帝为召告天下,在泰山举行祀典,他们在这里礼拜天地封禅后,就成了“天”的儿子,叫天子,也成了天下独尊的第一人,自誉“寡人”。管理芸芸众生。由此,泰山也成了“泰山之神”。《尚书》记载从夏、商、周己有在泰山的祭祀活动,但那时可能没有“庙”。也就是从“秦既作峙”,峙就是用土垒起来的台子。“汉亦起宫”,才有了“庙”的雏形。以后,唐代增修,宋代扩建,到了北宋宣和四年(1122年)东岳庙已是“殿,寝,堂,阁,门,亭,库,馆,观,廊,庑”合百一十有三楹。成了我国现存相当规摸的宫殿式建筑群。以后的明,清各时期都有增修。目前,泰山脚下的东岳庙,建筑面积近十万平方米。设有三洞大门,南面主门为正阳门,两侧掖门有仰高门,见大门;东西两侧有东华门,西华门;北面有后宰门。严然是皇家的称谓。建筑群体以主殿天祝殿为中轴,周边有回廊环绕,钟鼓楼左右对称。院内有最早时秦二世泰山石刻,汉张迁碑,衡方碑,唐神宝寺碑及铜亭,铁塔。这些告诉人们,是有文字记载的证明。《史记,封禅记》记载了早前夏,商,周的王室在泰山封禅;尤其,是记载了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亲临登泰山及祭祀活动,汉以后历历代代的皇室也就纷纷效仿,恐不及致。据统计从秦始皇到北宋真宗,先后有六位皇帝多达十次,在泰山脚下封禅。其规模和声势可想而知。山东的东岳庙就成了他们此项活动的落脚地,既是他们的祀典活动的盛地,也是游玩休息的佳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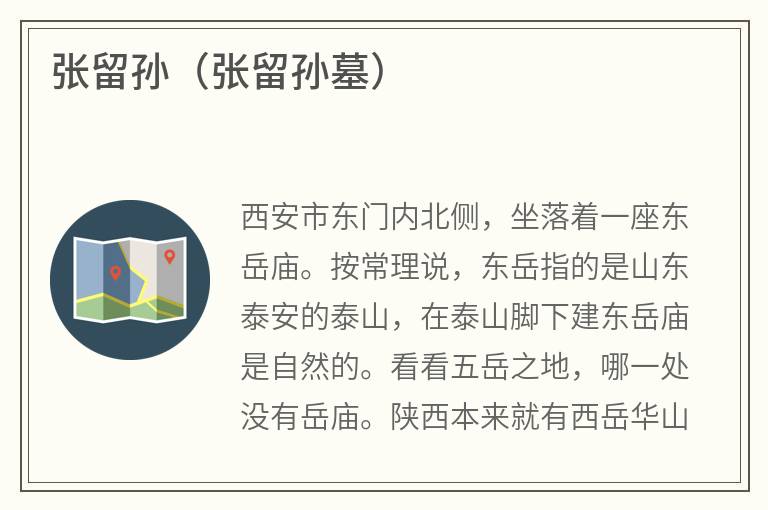
张留孙(张留孙墓)
北京的东岳庙在朝阳区朝外大街。这里的东岳庙是一座道观。传说西汉功臣张良的第八代孙,东汉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,受老子梦托创办道教自称正一派,即道教的开创者张天师。到了元代,他的门徒张留孙又独创道教的玄宗派。张留孙深得元世祖忽必烈器重,在至治二年(1322年)委以元开府阁三司上卿,虽然地位显赫,这位道教玄宗派大宗师独自出资与弟子吴全节建起元京都大都,也就是今天北京的东岳庙。
他们把泰山封为了神,并有了响亮的官称一一天齐仁圣大帝。这可能也是天底下五岳之山的神仙,都冠之以“大帝”的由来吧。那时北京的东岳庙,也叫仁圣宫。元泰和二年(1325年)元朝皇帝的女儿鲁国大长公主桑格吉刺捐资加盖了大帝的寝宫。让东岳大帝在北京有个休息的地方。明朝正统十二年(1447年),又补加两庑,设七十二司和帝妃行宫。这可能是东岳庙中最先出现七十二司和帝妃寝宫的源头。天齐仁至大帝管理囯家和涉足社会百姓生活气份出现了。清康熙(1608年)毁于大火。清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在保留元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,在东院加盖了娘娘殿,伏魔大帝殿,在东岳大帝身傍又增添了众多侍臣,紧邻此殿增设了玉皇大帝殿,药王殿;正院加修了戟门,岱宗室和育德殿。院内立着元代有名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《张天师神道碑》,也叫道教碑。这样看来,从元代到明、清,东岳庙中又配以七十二司和他行游时的帝妃行宫,给东岳庙和天齐仁圣大帝的文章就作得最全且最足了。
历史上北宋的京城卡梁在今天的河南开封,那里却没有东岳庙。那里距泰山近些吧。北宋致和六年(1116)却在千里之遥的西安建了个东岳庙。那时是什么样子,实在想像不出。明弘治年到清光绪年间重修后,正南为三大门,院内有大殿,中殿和后殿,东西两侧有长庑。也就是现在的东岳大帝殿,大帝娘娘殿以及最后边高基台上的帝妃寝宫。宫殿中的坐像己不复存在。东岳大帝是很辛苦的,以前是坐享其成,到此时要管理七十二司,要寻游天下,帝妃陪伴,必有寝宫。他们“西迁”到西安,只好把他管理的七十二司,以彩绘壁画的形式,留在了大殿的墙壁上。可谓应有尽有。这些壁画的内容围绕着东岳大帝,涉及传说故事,神灵崇拜,百姓生活,方方面面囊括无余。画面中的人物有252位角色,各式造型,举手投足,眉目神形栩栩如生;山水,楼阁等精致秀美。这种以“司”划分社会现象,应当是延用了北京东岳庙中表现方法。以“司”为管理单位的“网络”化,可谓是管理学科的一大发明。
“司”作为名词是一个部分的名称,作为动词是操作的意思。东岳庙中古人用的“司”,可能是双层含义。如“给药司”,从画面上分析,既是管理药品的部门,又是拿着药在发放的情景。还有些司,凿实令人匪思。
西安东岳庙壁画局部
和我同去参观的一位朋友,告诉我壁画中有个“司”叫“奸倭司”。那是些道德败坏,作风下流的人做着那些事。他说世上还就有这样的事。他小区邻居,自己与不三不四的男人常年鬼混,又共同设谋,让自己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姐姐,去探究在外地的姐夫,跟那里女人鬼混之事。她却在家堂而皇之的与那人鬼混。事情败露,相互指骂。旁人戏说,狗咬狗,两嘴毛,声名狼藉。这可真是奸倭事,就有奸倭司。
我和朋友都以为“司”里的事,只有我们周围才会发生,殊不知,有人的地方就存在。十八世纪,欧洲的一位哲学家阿图尔、叔本华,是这样描写他身处一地的情况。“他们窥探着,窃听着,关注着,所发生的一切。什么驱使着每一个人,每一个人做着什么,每一个人说着什么,无论高声地,还是轻柔地。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们的眼睛和耳朵,透过窗户,他们盯梢。他们的耳朵紧贴在门上,没有什么事情没被他们看到,没有猫能够在他们末察觉之时,就溜到屋顶上。为获知某人的心思以及价值,他们侧耳倾听。他的每年花费多大,以及他是否镇上的名流。他是否被率先问候,是“威风凛凛的大人”,还是仁慈宽厚的,是议员,还是教士,是路德教的,还是罗马天主教的,是己婚,还是单身的。他的房子有多大,他的衣服有多讲究,全部被精细地琢磨过。还是那个问题,他能为我们所用吗?这个问题同那些就伟大与渺小所做的考量相比,自然才是他们愿意考虑的事情。或者另一个被考虑的问题,他对我们的看法如何?他所想的和所说的是什么?他们询问每一个普通的无名氏,仔细掂量着对方的每一句话,他们眯缝起自己的眼睛。”……。当我将这位哲人的所说告诉朋友时,他惊讶地说,这不就是我们看到的东岳庙壁画上的“事非司”吗!
可叹,我们的祖先一千多年前,即将人类社会的班班桩桩以“司”的“网络化”的形式表现了出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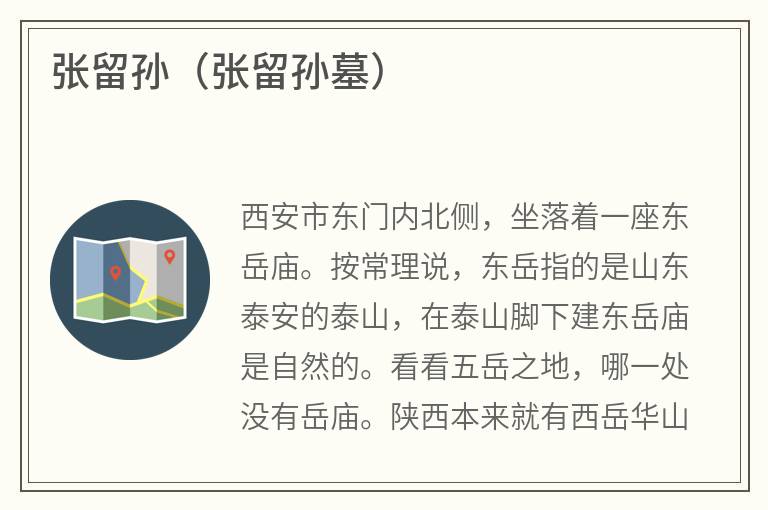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