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卜喜逢
一、《红楼梦考证》的论证过程
胡适将古典小说分为两类:逐渐演变出来的历史小说;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。基于不同的类别,胡适有选择地用不同方法来进行研究:逐渐演变而来的历史小说,运用历史演变法;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运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,在传记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、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。研究的共同点是版本,要做到“遍求别本”,而后“实事是正,多闻阙疑”。

庄绍光人物形象分析(庄绍光主要事件概括)
在确定了这些研究重点与基础原则之后,胡适对《红楼梦》进行了考证。1921年3月27日,胡适写成了《红楼梦考证》(初稿),作为亚东本《红楼梦》的前言。同年11月12日,写成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,据胡适自己说:“改定了七八千字。”二者之不同,主要是因胡适掌握的资料的扩充,从而导致了观点上的变化。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,初稿与改定稿之间并无区别。
我们且来看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中的主要观点;
1.以往的红学走错了道路,所作的并非是《红楼梦》的考证,而是《红楼梦》的附会。
2.在著者方面考证作者为曹雪芹名霑,汉军正白旗人,是曹頫的儿子,曹寅的孙子;曹家为织造世家,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,曹家极盛时曾接驾四次以上,终因亏空而被抄没;曹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(约1715-1720),死于乾隆三十年(1765)左右,作书时间约在乾隆初年至乾隆三十年;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,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,甄贾两府即是曹家的影子。
3《红楼梦》最初只有八十回本,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,始有百二十回本《红楼梦》。
4.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补作者为高鹗。
在这篇考证宏文中,胡适将自己总结的“科学方法”运用得淋漓尽致。他本着存疑的态度,审视了红学既往的研究,又从这些既往研究的方法入手,展开这篇文章。整体来说胡适在“归纳-假设-演绎"的方法之下,处处以证据来说话。他在批驳《红楼梦索隐》之时,借助于孟森《董小宛考》的考据成果,揭示董小宛与顺治帝之间的年龄差距;批驳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时,借用演绎之法,指出蔡元培研究方法的“猜谜”本质,等等。
如果说在第一部分中,胡适的方法只是牛刀小试,在论证《红楼梦》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说的过程中,则可视之为大展身手了。胡适通过周密的论证,凭借种种史料,以曹寅为线索,勾勒出曹氏家族的经历,又通过杨钟羲《雪桥诗话续集》中的记载,追踪曹雪芹的痕迹,最终考据出曹雪芹的大致概况。凭借这些归纳的成果,胡适得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自叙传的假设。而后又归纳演绎并用,进一步证实自叙传说。在论证后四十回作者的过程中,胡适仍然延续了这种做法:首先通过有正本与程本之间的版本差异,得出“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”这一结论,同时又因程、高序及引言中的“语焉不详”,使得胡适对“后四十回的著者问题”产生了怀疑。通过俞樾《小浮梅闲话》中记载的张问陶的诗注,得出高鹗是后四十回作者的假设,继而通过对高鹗的考证,以及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脱榫之处,用演绎之法来进行论证证实。这一部分的论证方法与第二部分几乎一致。
当我们进入到胡适的思考语境之中,我们就会发现,这个论证过程是非常成功的,是胡适所倡导的“科学方法”的成功演示,可称之为考据文的典范。
排除版本及后四十回著者问题,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前部的重心在于对作者以及《红楼梦》之内容两部分,有着两个层面的结论:
其一,曹雪芹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,此为史学的考证。其二,《红楼梦》是自叙传说,是“自然主义”的杰作,这是胡适对《红楼梦》文本内容的判断。
从论证次序上看,作者的考证是服务于自叙传说的,此种做法,原因是多层面的。首先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一文,第一部分是对红学索隐的总结与批判,而红学索隐的研究本身是为了探求《红楼梦》是写什么的问题,即“本事是什么。“自叙传说”的提出,可看作对索隐红学的回应解决的同样是“本事”问题。在《跋〈红楼梦考证〉》一文中,胡适写道:“我以为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。”此语正可说明“著作之内容”是考证的目的。
另一方面,这又是胡适研究个性的体现。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我们寻出胡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目的。目的会是他挑选研究对象的主要因素。但当深入到研究本身时,研究个性反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在胡适身上,我们会发现他的研究偏重于证实,一切都围绕证据而来,当胡适沉浸到《红楼梦》研究之中时,这种研究个性就会凸显。胡适自称有着“考据癖”与“历史癖”,这深深地影响到了他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过程,尤其是生成假设的过程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文中,“曹贾互证”的部分正是被作为证明“自叙传说”的证据,这正可说明此问题:要给“著作之内容”找中实际的来源
胡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目的是“本事"的考证,但在这“本事”考证过程中,实际也是对曹雪芹作者地位的加强论证
关于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考辨,从方法上来讲,同样是以“怀疑”的态度,归纳、假设与演绎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论证的,其疑点之始,固是在于程伟元、高鹗的记述以及俞樾的《小浮梅闲话》,其论证之最主要者,却是因其不合于自叙传说的整体结论。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一文末尾处写道:“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——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《考证》以来,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----也许有将来发现新证据后即需改正的。”红学发展至今,胡适的许多观点有了修正,如高鹗续书说等。但我们修正他的这个结论时所运用的方法与胡适是一致的,亦可视作对胡适观点的补充。
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一文是有着奠基作用的,它一方面建立了以考据为主要方法的研究范式,另一方面又形成了“本事”考证为目的的文本阐释模式。从结论上来说同样有着重要意义: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,确立了高鹗的续作者地位。同时在胡适的引导下,家世与版本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要领域。
二、《红楼梦考证》的得失
胡适以“科学”原则提炼乾嘉朴学的方法,而后将这种源于治经史之法来作小说研究,这对小说作者、版本、时代等方面的探索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。正如陈平原先生在《胡适文学史研究》一文中写道:
一旦胡适将小说作为与传统经学、史学平起平坐的学术主题,必然以清儒治经史的方法治小说。以本事考异与版本校勘为根基,再贯以历史的眼光与母题研究思路,如此中西合璧的学术视野,使胡适得以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纵横驰骋。
从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的结论来看,有关于曹家家世的部分内容,以及《红楼梦》作者为曹雪芹等结论是坚不可摧的,这些考证成果奠定了红学文献的基础。虽然目前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有着诸多说法,然而这些说法大多建立在比附的基础上,依附于胡适所批判的猜笨迷,与胡适严谨详密的论断自不可同日而语。
单纯从考证来说,胡适延续了乾嘉朴学的方式。乾嘉朴学继承汉儒治学方法,注重小学训诂,却又从未忽略对义理的追求,如朴学大家戴震认为:“故训明则古经明,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,而我心之所同然者,乃因之而明。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,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。”由此可知戴震态度:由考证而至义理,考证是明义理的手段与途径。与戴震观点相同,钱大昕在《经籍篡诂·序》中亦曾言:“有文字而后有诂训,有诂训而后有义理。”这与戴震的认知途径是一致的。胡适同样继承了这一点。如果将乾嘉朴学对义理的认知转移到小说研究之中,则义理可视之为小说作者的创作主旨。针对于此,在做完考证工作之后,胡适得出了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的结论,并进而认为《红楼梦》是自然主义的杰作,是“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‘坐吃山空’‘树倒猢狲散’的自然趋势”,这与朴学的认知过程是相同的。
然而《红楼梦》并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,更不是“自然主义”的杰作,此为学界共识,自不必多说。可为何胡适会得出如此结论呢?笔者以为,这有两方面的原因:
其一,胡适的方法固然是科学的,但是方法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。以治经史之法,来证小说,则小说在研究者的眼中,必然呈现出经史的特征,从而忽略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特性。陈维昭先生在《红学通史》中曾将新红学的本质认识为“实证”与“实录”的合一,笔者是十分认同的。由实证而出,必得实录的结论,这正是方法决定结论的表现,这其中却是因“实”而生的。胡适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,他在《问题与主义》中倡议:“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,那个问题如何解决,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,那种主义如何奥妙。”这种言论尤显胡适研究的倾向性。也正是这种偏重于实,以实证作为研究手段的做法,使得他有着对“虚”的回避。在他的小说研究之中,如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等,均是如此。或因“诗无达诂”的缘故,小说本身的艺术研究无法证实,导致了胡适的“避虚就实”,这是胡适个人的研究个性决定的。
另外,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的传统,也是原因之一。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有诸多说法,然总不脱稗官、史传、诸子、神话、传说、史话诸种,这其中均有史的成分,呈现出文史皆俱的特性。在此传统影响之下的小说创作,自可被证实,如《孽海花》中的陈千秋即田千秋,孙汶即孙文,又如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马纯上即冯粹中,庄绍光即程绵庄。因着这种创作传统,关于“本事”的研究才会出现,自传与他传之间,考证与索隐之间才会形成攻驳之势。两者之共同点皆为求“实”然而又皆弱于“虚”。
相比于《儒林外史》《孽海花》等“实”的成分比较大,《红楼梦》却是“虚”的成分更多一些,这就在于《红楼梦》高度的“典型化”,“本事”考证实为反“典型化”的,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去思考《红楼梦》到底写了谁家事,却忽略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,从而在根本上混淆了素材之于小说的关系。鲁迅曾因胡适纠结于谁是贾宝玉的模特,而称其为“特种学者”,实已指出此种研究方式的偏颇。鲁迅认知中的创作模式当分为两种:
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,有两法。一是专用一个人,……二是杂取种种人,合成一个,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,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。……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,例如画家的画人物,也是静观默察,烂熟于心,然后凝神结想,一挥而就,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。
这正是典型化的生动表达。而胡适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《红楼梦》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不同,从而走向了证实的道路,陷入了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的认知之中。
其二,胡适的考证手段来源于乾嘉朴学,清代早期的学术中与朴学相对应的是桐城派,二者之间论争的根本是“汉宋之争”,义理、考据与辞章之争等诸多范畴。戴震在《与方希原书》中写道“古今学问之途,其大致有三:或事于理义;或事于制数;或事于文章…..事于文章者,等而末者也。”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,在《复秦小岘书》中写道:“天下学问之事,有义理、文章、考证三者之分,异趋而同不可废。”这两段话正可反映二者对辞章的重视程度的不同,姚鼐认为三者当结合运用,而戴震视辞章为“等而末者”,这也影响了胡适研究的侧重点。胡适偏于“实”,而忽视“虚”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。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对“辞章”的认识不足所导致的。
何为“辞章”?钱穆先生认为:“至于所谓辞章,诸位当知,一番义理,即是一番思想,思想即如一番不开口的讲话。中国古人说:‘有德必有言’,言就该是辞章。”针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,钱穆先生有着深入的研究,他认为三者是不同的学问,辞章、考据、义理正是“今天文学院里文、史、哲三科”。同时,他又认为三者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,他在《学问的三方面》里写道:“任何一项学问中,定涵有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。此三者,合则成美,偏则成病。”此论确立了三者之间贯通的关系。在《学与人》一文中,钱穆又从方法论的角度说道:“考据应是考其义理,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。”由此可见,“义理”“考据”“辞章”是密不可分的。
回归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一文,胡适由“考据”直至“义理”,这是“自叙传说”乃至于“自然主义杰作”这一判断产生的内在逻辑,之间没有对“辞章”加以研究,这也是胡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一个弊端。缺少对“辞章”这一环节的研究,使得结论出现偏差。
结语
胡适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,在客观上提升了《红楼梦》的地位,从而使《红楼梦》研究脱离了戏说的语境,成为严肃学术之一种,这是功不可没的。新红学至今已有百年,百年间无数学人继承这种方法,投入大量精力对《红楼梦》进行考证,成果斐然,这也奠定了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文献基础,然而正如胡适先生自承的,自己所作的工作是“文学史”的研究,并非是“文学”的研究”,可后来者多继承了这种方法,却缺乏这种认知,针对于此陈平原先生曾说道:
这正因为胡适及其同道过于沉醉在以作者家世证小说的成功,忽略了小说家“假语村言”的权力,“红学”逐渐蜕变为“曹学”,“自传说”引来越来越多的批评。
陈平原先生可谓一语中的。在胡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诸多学者皆本着本事考证的目的,进行大量的研究,时至今日,此种做法仍有延续。又因如此,红学的侧重点转移到考证曹雪芹及曹氏家族之上,而囿于曹雪芹史料的匮乏,考证重心继续产生了偏移,有着考证与《红楼梦》文本背离的倾向。
实质上这与胡适的考证目的不符。他虽承认自己做的是“文学史”的研究,这却是因考证为文章主体的缘故,毕竟在《红楼梦考证》(改定稿)一文中,缺乏文学性的分析,但他考证曹雪芹的目的,依然是为《红楼梦》的文本服务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的开篇他即确定考证的范畴为“著者”“版本”“时代”,其目的却是“真正了解《红楼梦》”,自叙传说的结论亦是针对文本而来的,这种目的性就非常明确了。在1921年4月27日的日记中,胡适有这样一段话:“既已懂得《诗》的声音、训诂、文法三项了,然后可以求出三百篇的真意,作为诗的新《序》。”这与他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的过程是一致的。考证的虽是著者、版本与时代,目的却是文学性的研究。
百年荏苒红学已成显学反思过往才能清晰认知未来。我们固不用如俞平伯先生一样将考证视之为黑漆,却也应知考证对于文学的作用及局限,用合适的方法,研究适合的领域,以图红学新时期更大的发展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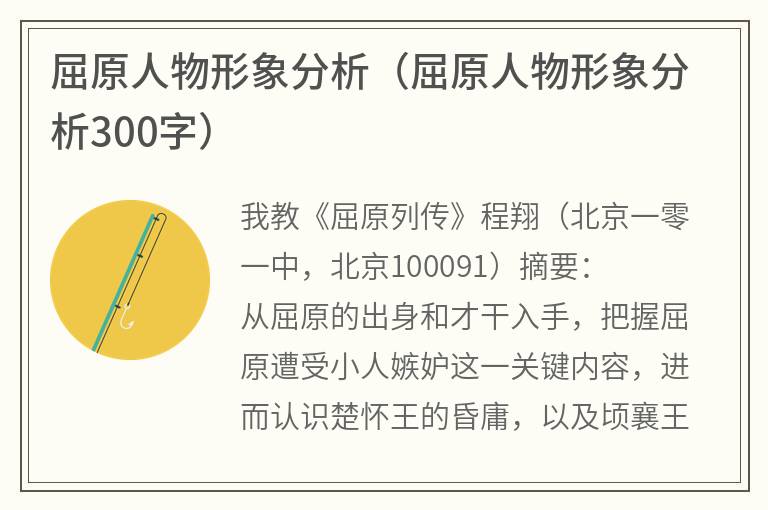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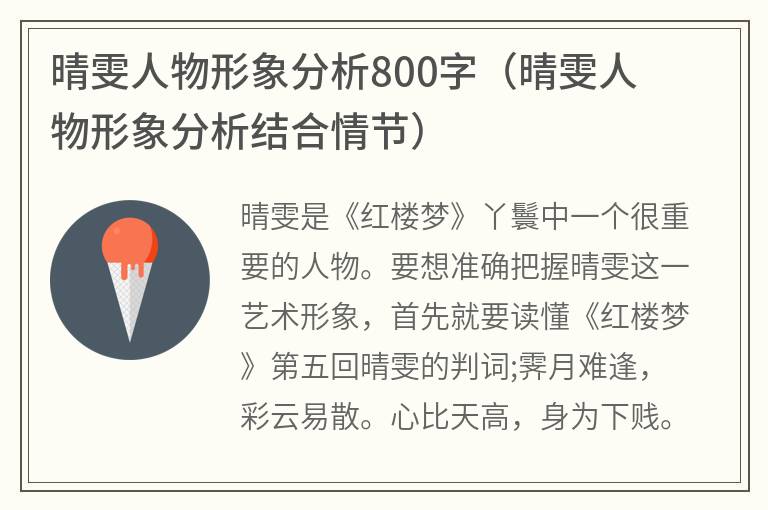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