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另一株也是枣树”,鲁迅先生《秋夜》里的两株枣树让当年的我十分困惑,大作家行文这么啰嗦?虽然不解其意,却因而想到了我家的大枣树,依葫芦画瓢写到“在我家院子西侧,可以看见牲口棚旁有一棵树,远看是枣树,近看还是枣树”。
桃三杏四梨五年,枣树当年就还钱。在农村桃、杏、梨等果树并不常见,唯有其貌不扬的枣树低调地扎根在屋后房前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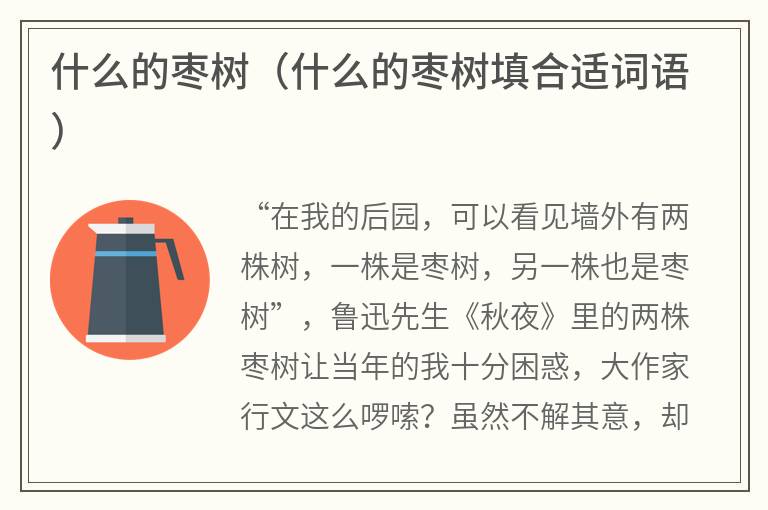
什么的枣树(什么的枣树填合适词语)
我家这棵枣树比我年纪还大呢,是伯父家的三哥种下的,到我小时候,已进入盛果期。
它偏于一隅却十分引人注意。树干粗大,直径应该能达到25厘米。灰褐色的树皮到处裂着嘴儿,粗粗拉拉、疙疙瘩瘩的。在约一米五高的地方,分裂成三股粗壮的分杈,又生出无数粗细不等长短各异的枝干恣意地向四面八方散去。夏秋季枝繁叶茂,树冠齐整浑圆不偏不倚。在我心里,村里没有谁家的枣树比我家这棵更高更壮更好了!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在我们的小院里,知春最早的就是枣树了。不知是一夜春风,还是一场春雨,把冬眠三个月的枣树叫醒了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灰乎乎光秃秃直挺挺干巴巴的枝枝杈杈忽然间就柔软了,欣欣然吹着煦风沐着细雨。“远看近无”的鹅黄浅绿鼓胀胀地充盈了每一寸树皮。清明过后,嫩绿嫩绿的娇小叶片星星点点缀满枝头,迎着春日细碎的阳光,整个树都光光鲜鲜,亮亮闪闪,有如无数个小镜子映射着晶莹的光影。
每次走出房门看到它,年幼的我心里都顿时升腾一种不寻常的情愫。那就是“满怀希望”的感觉吧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天气热了起来,枣树长出了如小米粒般玲珑的花蕾,开出了黄绿色的小花儿,一堆堆一簇簇,密密匝匝地掩藏在油亮亮的绿叶中。
“牡丹花好空入目,枣花至小能成实”,枣花摇落后结出了青青的小枣。
七月十五红边儿,八月十五落杆儿(农历)。枣子由青转红,一串串压低了树梢。最低处,我们伸手就能够到。
然而我们姐仨儿却不为所动,极少采摘。妈妈没有开宗明议地禁止过,我们却已早早察觉到她对这些枣儿的爱惜,都默契地守护着一个信条儿:枣儿不能当零嘴儿随意吃,等它熟透了,才能有更大的价值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“小姑儿,我能摘几个枣吃吗?”,比我还大一岁的侄女可怜巴巴的,“不行!”我这个小老姑板着脸一点儿也不松口儿啊。
今天你摘几个,明天她摘几个,低处的摘完了就该摘高处的了。自家人摘了,街坊邻居也就跟着摘了。那个时候虽没听说过“破窗效应“,但十来岁的我已经悟到这个理儿。
“你家的孩子咋这么有出息?一点儿都不馋呢!”妈妈的老姐妹儿来串门夸奖道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我们不馋,可馋坏了别的小孩儿,隔着院墙,望枣兴叹。气不过时就狠狠地朝树梢砍上几块土疙瘩小石子,妄想砸掉几颗枣儿,可惜不是没砸中,就是枣都掉到院墙里了,哈哈哈。
这种情形南宋诗人辛弃疾也遇到过,其诗云:“西风梨枣山园,儿童偷把长竿,莫遣旁人惊去,老夫静处闲看”。这威武大将军出身的老头儿也有可爱厚道的一面啊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不但不摘枣儿,我们甚至走路都躲着,不从枣树下面过。因为枣树上有惹不起的小家伙儿——八角子,一种绿色身带长毛儿的软体虫子,学名刺蛾。不要说被它蛰到,就是风把那毛吹到身上都受不了啊。那种怪异的疼,一阵阵的,比针扎还难受呢,几天都好不了。
除了“八角”,枣树枝上还长满硬挺挺的“刺”,长的能有两三厘米呢,非常尖锐,离树近了也得小心被扎到。有时夏天煮田螺,手边没有缝衣针,就到枣树上撅几段带刺儿的树枝,用它的刺挑田螺肉吃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八月十五到了,树上的枣儿大部分红透了,红彤彤的如玛瑙,终于可以“落杆儿“了。
挑一个周末的清晨,我们早早地起来。
妈妈取来长长的竹杆、木棍,啪啪啪,一下下往枣树上打。噼里啪啦声中大红枣和着绿叶子、树枝纷纷落下,跳跃着翻滚着。有的掉在地面,有的落在驴棚上、猪圈顶子上,有的滚到犄角旮旯里。我们拿着大大小小的家伙什儿,四处捡拾。“哎!这儿有个特别大的!呀!这儿有个特别红的!”,不时兴奋地发出一声声惊叹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一个小时后结束战斗。被洗劫后的枣树枝朗叶疏,零星漏网的枣子像顽强的士兵,擎着面小红旗坚守在高地。
眼前的几大盆红枣亮晶晶的。稍作休息,我们再花功夫把红半边儿青半边儿的枣儿挑出来。青红相间的枣儿口感并不比全红的差,反而更脆爽些。这些枣儿被分成若干份儿,送给左邻右舍和本家们尝尝。
我们又挑出几捧内外无伤,硬实饱满的枣。水洗后风干,小碗里倒白酒,每个枣儿都在里泡一下,分装进大罐头瓶子里,拧好盖子,放在阴凉处。半个月过后开封——醉枣做得了!果皮红润更有光泽,没有一点儿褶皱,枣的甜与酒的香交融,别有滋味啊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其余的大红枣儿,妈妈把它们摊晒在外窗台上。外边用木棍拦住,隔一两天用手翻搅翻搅。晒的分寸很重要,时间短了容易坏,时间长了,枣肉就太干巴了。妈妈总要捏捏尝尝,鉴定晒好了,才装到家里两个圆圆的大竹筐子里,挂在厢房横梁垂下的铁钩子上。收成好的年份能有二十来斤的干枣呢。
记得有年冬天,村里一个姨受亲戚之托寻摸儿两斤红枣,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家。妈妈笑脸相迎,满口答应,给称足了两斤枣儿。那个姨拿出几块钱来要“结账”,妈妈赶紧推让。一个攥着钱往口袋里塞,一个抓着对方的手不让。两个人拉拉扯扯地在屋子里玩儿起了太极推手,我们在一边饶有兴趣儿地观战。“快拿着!我这也是帮人家买!”,“别让我着急!我不是卖枣儿的,给钱还不卖呢!”。直到俩人累得脸红脖子粗,妈妈才终于胜出!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即使一个冬天都没有零食,我们的“有出息”还在继续——不会去打干枣的主意。
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稀罕,一是不容易买到,二是也没闲钱买“可有可无”的吃食。鲜枣是水果,干枣是零食,只有和主食搭伙儿,枣的功能才算是到了极致。
腊八节前一天,妈妈把竹筐取下打开,取出一些红枣,还是分成好几份儿,相好的人家每户送去一瓢。第二天熬腊八粥,红枣是必不可少的,缺了它,粥就少了一股浓郁的枣香了。吃腊八粥时,妈妈还会一本正经地搞一个特别的“仪式”——把浓稠的粥抹一团子在枣树杈子上,犒劳一下这位默默无闻的功臣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年根儿到了,枣儿的重头戏才算真正登场——蒸年糕。黄粘米磨粉加水拌匀,煮红豆,泡大枣。一部分红豆和枣拌在面粉里,蒸前屉布上先密密铺上一层红豆大枣,再倒上厚厚的面粉,最上面同样均匀地盖上一层枣和豆,这个年糕才算完美了。
年糕要蒸好多锅,红枣的用量是巨大的,竹筐里所剩无几,这是我家枣最豪华的用处了。
好在春天快来了,又可以期待下一个收获季。
(图片来自网络,侵权删除)
离开老家三十来年了,老宅子连同那棵枣树有了新主人。前些年回去时,特意从院墙外往里望,枣树竟然小得快不认识了。只有单薄的几个枝杈落寞地伫立在风中。心中如梦般愰惚,这还是我家的枣树吗?
前些天,偶然提起,妈妈说新主人盖厢房时已经把枣树连根刨了。
呜呼!痛哉!
枣树!我家的枣树!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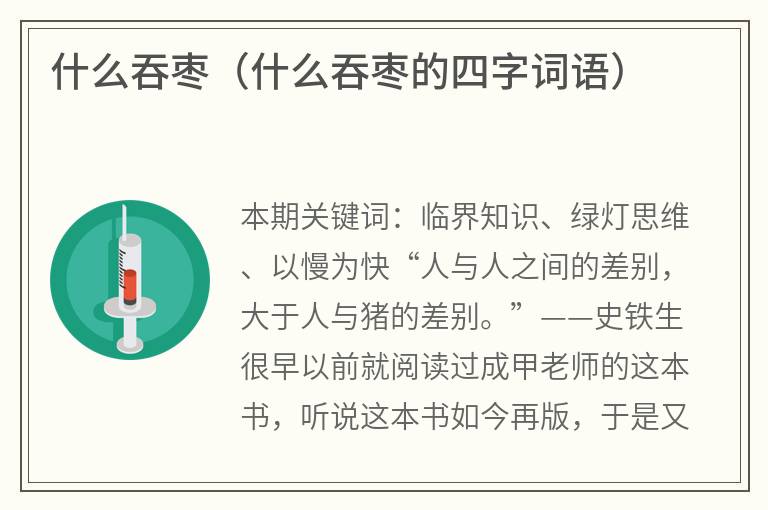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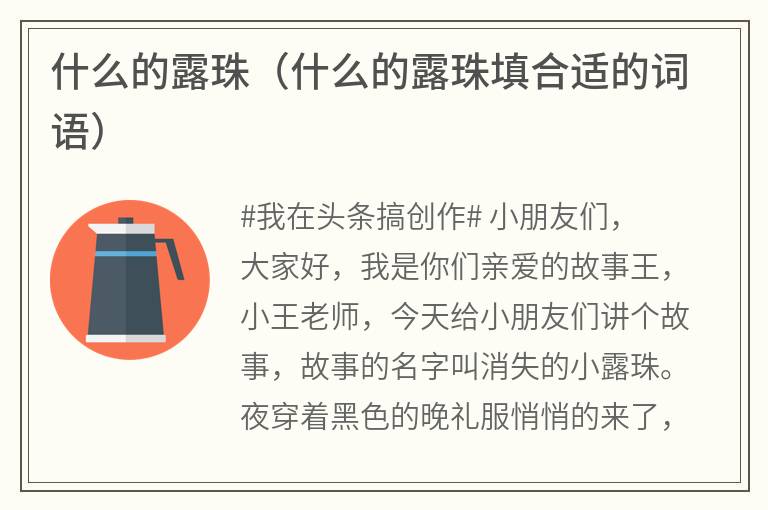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