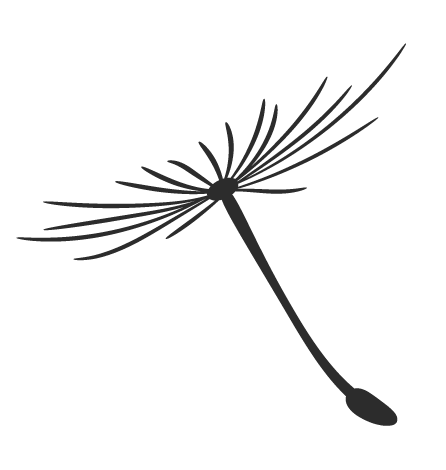
服饰问题,有如围城,学堂外面的人,欣赏女学生装束的清纯,可女学生们,却向往着世俗的艳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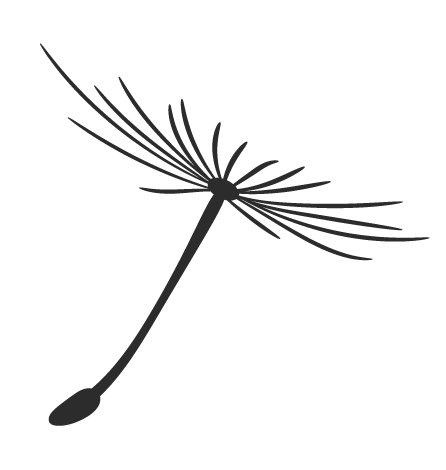
文/周松芳
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84篇文章,全文大约1200字,细读大约需要5分钟。
当年的女学生装束,在国中颇有横空出世之概,其实是从日本“拿来”,自然颇受多从日本留学回来或多受日本影响的新派人物的欢迎,而于旧式人物,则颇不以为然。女学生装束,除白衣黑裙外,在发髻上戴蝴蝶花的东洋发式,及好施围巾两个特征,均曾受人讥嘲。调侃发式还好,不过讥其徒有其表:“当头新髻巧堆鸦,一扫从前珠翠奢。五色迷离飘缎蝶,真成民国自由花。”调侃围巾,则颇恶毒,讽如自缢的杨贵妃返魂:“两肩一幅白绫拖,体态何人像最多?摇曳风前来缓缓,太真返自马嵬坡。”(《申报》1912年3月30日谷夫《咏沪上女界新装束四记》)

服饰问题,有如围城,学堂外面的人,欣赏女学生装束的清纯,可女学生们,却向往着世俗的艳丽,在时髦风盛的上海尤甚。相对保守的北方人尤其看不惯,认为“女学生之服装所以特成一格为人所重者,在其富于中和性与天然性”,像上海女学生服装,富贵华丽,像是二奶与三陪(姬侍)的行头,“最为失之”。(《北洋画报》1930年第539期轩渠《记辽宁女生之服装》)而最令人头疼的是,女学生要做操,做操要穿裤,但是此前除了妓女,良家女子是不穿裤的。这让女学生们捡了个大便宜。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荪就回忆说,她1904年在长沙读书时,“每日有体操,并定制操衣,每日四点钟放学后,便操瑞典柔软操十分钟,我们因有操衣穿,也很发生兴趣”。(《曾宝荪回忆录》)上海如此,广州亦然。所不同的是,上海患的是“富贵病”,广州得的是“革命后遗症”,女人们乘着革命的东风走上街头,服式也“革命”到古怪的程度,惹得女学生亦纷纷效法,连革命当局都看不过眼,“教育司以此等服式,令人鄙视,殊非女学生所应为”,意欲规训惩罚。(上海《教育杂志》1913年第4期《取缔女学生之服装》)

对女学生服装的规训,当局一开始即意识到了,早在1911年9月3日即发布了《学校制服规程令》,规定“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”,“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,裙用黑色”。此外,还不得烫发,不得穿高跟鞋等。但对于因操而着的裤装,却也只能网开一面。即便在革命改元以后,面对“革命性”的反弹措施日趋严厉的情形下,在革命首义地武昌,也只是规定“女生褂裤,俱用竹青洋布,褂与膝齐,裤须没胫。”(《取缔女学生之服装》)压力总会寻找缺口,有的学校趁机规定操衣上装短袄束腰带,下穿裤子以带绑束,使操衣渐成常服。一旦成了常服,制作便加用心,“式样十分漂亮,领、袖、裤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,穿上十分威武”,“学员有终日穿操衣上课者,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者。”(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(七)俞子夷《蔡元培与光复会革创时期》)

相对而言,革命策源地的广东,在服饰风气上反而转趋保守,言辞上严厉不少,对裤装不稍加通融。如教育厅发布的规训布告说,“人格尊贵之学生,身佩襟章”,却效“举止佻达,长袜猩红,裤不掩胫”的“无知识者”,“殊非自重之道”,故尔严令女学生“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”,务求“贫富能办,全堂一致,以肃容止,以正风尚”。(《取缔女学生之服装》)其实,这也不过是官场的明规则;潜规则中,女学生裤照穿,当局也莫可奈何。
本文作者周松芳,文史学者,专栏作家。曾就读于中山大学,现居广州。
图片来自网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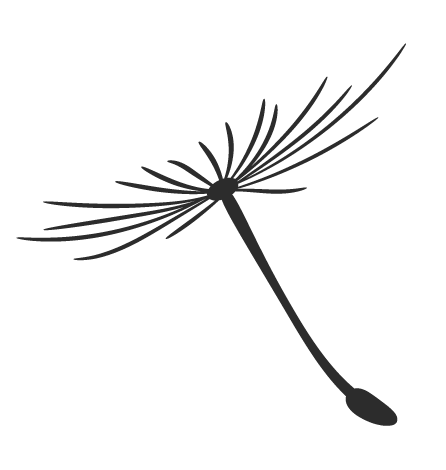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